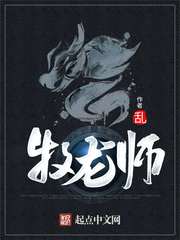天天看书>四合院:淮茹笑夫,谢不嫁之恩 > 第465章 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(第1页)
第465章 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(第1页)
秦淮茹顺着李子民手指方向,只见远处一条干涸近半的河流边,一个人影钻进了青纱帐。
“李大哥,看错了吧?这离京城,有十多里地,东旭怎么可能跑这么远?”
“他吃啥,喝啥,住哪?”
李子民也不纠结,重新启程。
秦家村。
“哟,这是老秦家的闺女,秦淮茹吧?你怎么和李子民一块回来了呀?”
一个老人瞅见李子民带着秦淮茹,眼珠子瞪得老大。
当初,
两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,又是悔婚,又是验身,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到现在,还有人时不时聊到。
“秦淮茹,你怀里的娃娃该不会是李子民的吧?听说,李子民有两个娃娃。。。。。”
“。。。。。。”
村里人越说越夸张,越说越狗血,秦淮茹绷不住,忙解释,“张家婶子别瞎说,这是我和东旭的孩子,今天回村里办事,李大哥正巧顺路,带了一脚,我们没关系是清白。。。”
李子民脸皮厚,懒得解释,见秦淮茹被本家几个长辈拉着说话,他先去了三婶家。
刚秋收完。
秦京茹一家子都在,瞧见李子民来了,三婶又惊又喜,“孩子他爹,快去杀鸡。”
“媳妇,你忘了吗?都吃大食堂了,咱家养的鸡早让大队收了去,我上哪抓?”
“哎,大食堂一天不如一天,我看用不了多久,就得散伙。”
今年北方干旱,种的小麦,玉米产量缩减了不少。
加上去年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,许多田地,没有人耕种,荒废了不少。
村口,留下不少标语:
“敢想敢干向前闯,亩产八千响当当。”
“土地潜力无尽藏,万斤亩产轻松创。”
“社员齐心力量强,亩产两万粮满仓。”
最狠的一条是,
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,亩产十万不稀罕。”
现在小麦受限于种子,肥料,农药,科学种植,正常年景亩产量在150斤上下。
能达到300斤产量,就算高产田了。
“唉,今年粮食歉收,公分也要打折扣。不让养鸡,养鸭,说好的自留地,也不让用。”
“食堂的伙食一天比一天差,去年隔三差五吃一顿肉,今年是想都别想,连油星子都闻不到。”
三婶碎碎念。